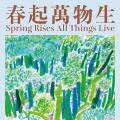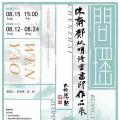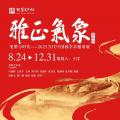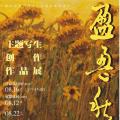【谈艺录】
东北抗日联军的事迹与杨靖宇将军这一人物形象,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中颇具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历史题材我关注已经有几年时间了。首先我是被其英雄事迹所吸引,其次是觉得这个题材特别适合用油画去表现,这些处于寒冬季节里的人物造型、道具、环境及其色彩都特别有油画味儿。原来已经有不少艺术家画过相关内容,那么如何避免已有的创作模式,从新的角度去表现这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一直是我在思索的问题。
早在2013年冬天,我自己就到长春等地去考察过杨靖宇将军和东北抗联的有关事迹,搜集相关创作素材。我阅读了相关的人物传记和史料,到过东北抗联纪念馆和杨靖宇将军牺牲的地点,观察自然环境,也间接地感受到了彼时战斗的血雨腥风。杨靖宇将军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抗日名将,他身高一米九二,身材魁梧,相貌英俊,是一个天才的游击战大师,有着传奇般的战绩。他领导和指挥抗日联军第一军在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日军的疯狂围剿下,与日军周旋搏杀了十年,他领导的抗日活动发挥的军事作用和政治影响震惊中外。从战略上讲,他扼守住了日军战败将从陆地上撤退的咽喉要道,死死拖住几十万关东军,让他们不能出关作战,极大地减轻了内地战场中国军队的军事压力,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在断粮五天五夜的情况下,与日寇战至最后一人,誓死不降,壮烈殉国。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肠胃,发现里面没有一粒粮食,只有些许的棉絮、树皮和草根。在场日军无不为之震撼、胆寒,向他致敬。
杨靖宇将军是中华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以前关于这个题材的创作也大都注重表现英雄的牺牲场景;但同时,杨靖宇又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他体恤下属,关爱部下,对战士们有慈父般的爱。我在创作开始时曾想另辟蹊径,选择他最后和大部队情深义重、难以割舍地分别的情节来表现,但这个方案并不能表现杨靖宇作为英雄人物最本质的那一面。后来,我又想通过表现杨靖宇牺牲后各色人等的反应,来反思他牺牲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但创作也没能继续深入。
我在本次创作过程中有幸得到全山石先生的亲自指导,全先生给出的建议是,让我弄清楚这个人物到底有什么特点,他与别的英雄人物的区别在哪儿,人们为什么能够记住他,他的人生最为感人的事情是什么,他因何而辉煌。我说还是因他的牺牲太壮烈。他说:“对,还是要去表现他的牺牲,要抓住这个主题。”此外他还建议我用三联画的形式来概括表现杨靖宇将军光辉战斗的一生,中间是表现主人公牺牲前面对敌人英勇不屈的英姿,左右两幅分别是表现抗联与日军激烈搏斗以及部队在冰天雪地中夜晚宿营的场景。这个设计是典型的欧洲祭坛画样式,这样就和以往的同类题材作品拉开了距离,产生了新的视角。
全先生在塑造英雄人物方面有着非常独到丰富的经验,他告诫我在创作中不必完全拘泥于史料,要去表现“历史的真实”,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杨靖宇牺牲前在搏斗中左腕受伤,仍坚持用左手持枪与敌作战,我照此情节设计了许多动作,均不理想。全先生一再给我提醒,要表现英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毫无惧色,勇敢地“面对”敌人,而不是去表现人物战斗负伤后在战术上的“躲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从艺术表现上讲,这就将人物从“历史叙述”中解放出来,从而把问题的重点放在了表现人物的英雄气质上,这应该是一幅精神性的肖像。在动作细节上,我大胆摒弃左手负伤这一环节,让之左臂抬起扶靠大树,目的是加强人物四肢动作变化的幅度,增强艺术感染力。如此,人物动作的设计逐渐清晰起来,人物的整体动作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符合英雄人物在人们心中长留久驻的愿望,杨靖宇将军身体背靠大树,四肢变化富于节奏,动作具有一定的张力,还有一种壮美之感。对于人物动作设计的突破,让我感到在历史画的创作中,要很好地处理史实与艺术表现之间的分寸,才能给想象力和艺术语言发挥的空间。
油画创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创作者对主题不断理解深化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把作品推向成熟。一件作品的形成是多方位的,人物设计固然重要,但人物周围的环境同样应当得到关注,才能展现特定的氛围,产生与主体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中间这幅人物的设计与刻画是“独角戏”,巨大的画幅中,周围的空间与环境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面积,弄不好就空掉了。在以前表现英雄人物的油画作品中,往往选择重或深灰背景来表现一种压抑与悲壮的气氛与情绪,这幅作品在最初,背景设计也是低视角下的风雪密林和较灰暗的天空,但画来画去总有一种舞台布景的感觉,很单薄,没有油画的丰富感和厚度,人物融不进环境中。后来,我从搜集的素材中发现了一个积雪从树上滑落的细节,似乎有了茅塞顿开之感。落雪有动势、有声响、有色彩,它从大树上轰然跌落,飞溅而下,狂飙自为英雄落,正好暗合了杨靖宇将军的牺牲“惊天地”这一意境要求,也实现了“高、亮”的色调设计,更使画面产生出一种浪漫的诗意,我就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造型与色彩因素强化出来。事实证明,运用高亮色调,也同样可以表现出主题的深沉悲壮。
此后,我又将日军的包围态势加以强化,日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被英雄的气势所慑,不敢靠前,从而达到“泣鬼神”的艺术效果。这样画面的主要结构就是“一横”“一竖”,一个重灰色的纪念碑矗立在大雪纷飞的林海雪原中,这个意象的形式结构也有了鲜明的象征性。
左右两幅的制作,由于时间不够没有能够完成,是为憾事,只好留待以后了。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全山石先生不顾年事已高,身体力行,把多年积累的艺术经验无私地传授,让我深为感动。我也要感谢给予我宝贵建议的靳尚谊先生、詹建俊先生、钟涵先生,以及为我的创作付出心血的胡振宇先生。我对历史画创作一直怀有敬意,这是一次难得的宝贵机会,我从中不断学习,积累创作经验,觉得收获甚多。
(作者:李前,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