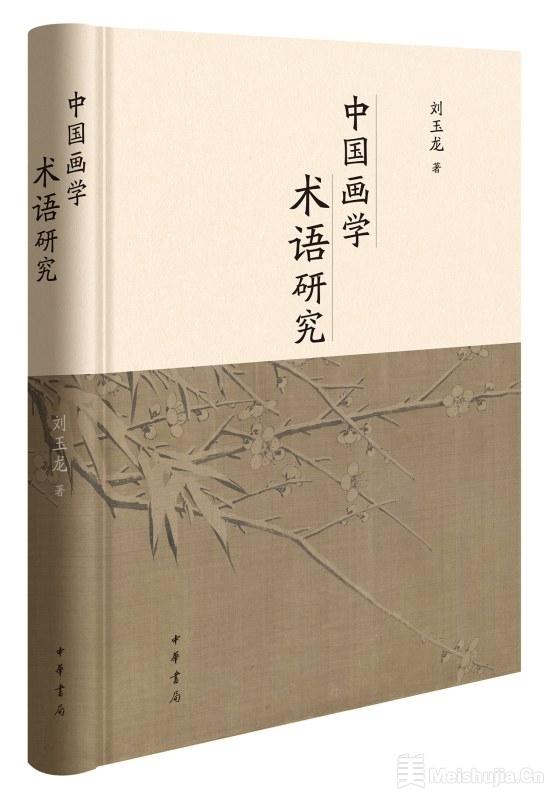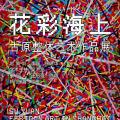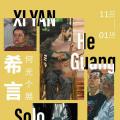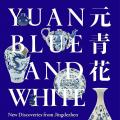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常听到关于“传统与现代如何结合”的讨论。而在中国画领域,刘玉龙所著《中国画学术语研究》恰似一座精心设计的立交桥,将古老的中国画传统与现代艺术世界巧妙地连接了起来。这座“桥梁”不仅有助于我们在传承中不迷失方向,更为中国画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
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首先需要什么?一张准确的地图。对中国画而言,那些专业术语就是这张地图上的重要地标。“笔墨”“气韵”“写意”“丹青”……这些词语看似简单,却是理解中国画的钥匙。《中国画学术语研究》就像一位资深的向导,带着我们在这张“语言地图”上细细探寻。例如,“笔墨”一词,远非仅指毛笔与墨汁这般简单。它涵盖用笔的力度、节奏,用墨的浓淡、干湿,更承载着画家的修养与情感。正如音乐家的音符、作家的文字,“笔墨”是中国画最基础也最富表现力的语言。再如“写意”,常被误读为“逸笔草草”。实则,“写意”重在“以形写神”,不求外形酷肖,而重捕捉对象精神内核。齐白石画虾,寥寥数笔,便将虾的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正是“写意”精神的完美诠释。
传承与创新:中国画的两种力量
中国画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始终坚守传承。这两股力量,缺一不可。
传承是在古人的智慧中扎根。《中国画学术语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的大门。通过系统梳理这些专业术语,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古人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追求。以“丹青”一词为例。最初,“丹”指朱红色,“青”指石青色,二者皆为古代绘画中常用的矿物颜料。后来,“丹青”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代称。这一词的演变,本身就记录了中国画从注重色彩到崇尚水墨的发展历程。理解这一过程,我们便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画的独特韵味。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师古人”与“师造化”。这是中国画传承中的核心理念。“师古人”即向前辈大师学习,“师造化”则是向大自然学习。历代大师都强调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明代画家董其昌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
创新是在时代的土壤中生长。传统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条流动的河。中国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中国画学术语研究》让我们看到,每个时代都在为这条河流注入新的活水。“泼墨”这个技法,可以追溯到唐代的王墨。传说他酒酣作画,以头髻取墨,抵于绢素。这种看似随性的创作方式,其实包含着对水墨特性的深刻理解。当代艺术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出更加丰富的表现方式,让古老的技法接入当代的语言。另一个例子是“白描”。这种纯以墨线勾勒形象的画法,最早用于绘画创作的底稿。宋代李公麟将其发展成独立的创作形式,开创了中国人物画的新境界。到了当代,线条的表现力继续被拓展,艺术家们用个性化的线条语言,表达对世界的独特感受。
跨文化交流:让世界看懂中国画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画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障碍”。这个障碍不仅来自外语翻译,更来自文化背景的差异。
翻译的智慧在于两种文化间架桥。中国画术语的翻译是个特别有挑战性的工作。比如“气韵生动”这个中国画的核心概念,直译成英语很难传达其神韵。“气”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包含着生命能量、宇宙本源等丰富内涵;“韵”则关乎节奏、韵律、余味。这个词组整体上表达的是一种生命律动之美。《中国画学术语研究》在这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在跨文化传播中,简单的字面对译往往不够,需要辅以详细的解释说明。就像品茶,不仅要说出茶的名字,还要描述它的香气、口感、回甘,才能让没喝过的人真正理解。一个典型例子是“意境”的传达。这作为中国画追求的最高境界,不仅指画面本身,更涵盖画面所引发的联想与感受。在向外国朋友介绍时,可将其比喻为:不仅看到月亮,还能感受到月光的清辉,以此帮助他们理解这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独特审美。
通过精准的术语解读,中国画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国际艺术对话。例如,中国画的散点透视与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不同,它允许观者在画面中自由“游走”,这种多视点的表现方式,与当代艺术中的某些理念不谋而合。这些特色的准确传达,有助于打破“中国画过于古老,与当代艺术无关”的刻板印象,彰显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中国画独特的观察视角与表现手法,为世界艺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启发。
《中国画学术语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对过往的梳理,更在于对未来的启迪。它揭示出,传统并非压在肩头的重负,而是托举我们前行的基石。通过这些承载着千年智慧的术语,我们得以与古人对话,与今人交流,与世界沟通。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相信将有更多人通过这些“关键词”读懂中国画、爱上中国画。而中国画这门古老的艺术,也必将在新的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世界艺术园地增添独特的东方韵味。
(作者李宁系独立学者、书画史论博士,谢昀系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史论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