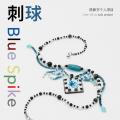【谈艺录】
一
世事皆循规矩,读《文会堂琴谱》,知弹琴也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些要求对琴师来说是一种制约,却又维护了其颜面与尊严。譬如有“五不弹”“十四不弹”之说——对俗子不弹、于尘市不弹、疾风甚雨不弹、不衣冠不弹,等等。可能是天时不对,环境不对,或者是人不对,那就不勉强自己,等待合适的条件。他们把弹琴当作一件庄重、清洁的事,有选择,有退让。
东晋的戴安道善弹琴,太宰司马晞请他去弹琴,他痛恨故作风雅、奢侈放纵的官僚贵族,于是拒绝,还把琴给摔了以表态度。戴安道的儿子戴勃承父艺,也善弹琴。中书令王绥请他弹琴,戴勃只是埋头喝粥,不想理睬。何时可弹,何时不弹,琴师心中明镜似的,总是有弹与不弹之选择。
与《文会堂琴谱》所言相似的有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他提出了“五乖”:心遽体留、意违势屈、风燥日炎、纸墨不称、情怠手阑。凡逢此,则不适于把笔挥毫,因为外在、内在都不畅适。
通常认为,已经掌握了弹琴技能、书写技能的人,到哪里都可以弹、可以写。然而与其随便、有求必应,不如有所制约,如此会使自己的追求更合于艺术创作的属性。
古人交集有限,活动有限,对书写会谨重一些。“敬惜字纸”的心理,也会使人小心地写,认真地写。“如对至尊”就是一种书写心理,使人有敬畏之心,书写恭敬,绝非儿童墨戏。而文人雅集以求放怀,面对同道、知音,纵笔当无妨。当书则书,不当书则罢手,理应如此。而后社会活动增多,书写亦成为一种应景形态,每个参与者都得动笔,不动笔则不循常理,也就不合群体气氛。
缘情而书,此为首要。能于书写中寄人之情、性之真、意趣之妙,为最佳。明人袁宏道认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一个人为情而趋赴是不由自主、不可阻遏的,这就使书写有了真切的表达。明人何良俊也有同感:“不本之性情,则其所谓托兴引喻与直陈其事者,又将安从生哉?”
所谓的“应酬”,不是手到情不到,就是手不到情也不到。或许技能见到了,情则乌有,也就寡淡无味。如果一个人习惯于应酬,缺乏写与不写之界限,其笔下就大都是属于技术活的产品,情意之作无多。临摹是以己心度古人之腹,由古人引领而下笔。创作则不同,全然独立而为,独立地思考其内容、形式,并以与其相符的心境、感受,规划整个过程。这个过程以情贯之,自然是情技合一,堪称“合作”。这样的机会当然不会常有。环境、心境也不会时常如此契合。一位书法家的临摹之作可以千万,下笔随时,而称“创作”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太多,需要期待。
少则得。适宜方下笔,方可写出心中之所求与指腕之灵动,达到自由自在。“吝书”也是一种态度,它是与无讲究对立的。所谓“惜墨如金”,正是“惜墨”,使书写者“吝啬”“俭省”,从而推辞、婉拒,表明一种审美态度。清人郑燮说,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郑氏所言于今也没过时。对书法家来说,笔墨是个人抒情写意的寄托,而非供他人玩好取乐,“不宜下笔”这点清高还是需要的。
二
从楷书入门素来为人认同——一点一画,有提有按,时轻时重,起讫有度,使四面停匀八边具备。如此,则一字平正舒展,如端人佩玉,穆穆雍雍。
有人以楷书为起点,倾心不移,便一生学楷写楷,成为楷书好手。如果专一于楷书,追楷法于极端,也就笔下见精到、精美、精工、精湛,透幽贯密,的确是一种工笔精神,这是以理性来延伸的。所谓“功夫”,从楷书就可以判断其深邃或浅率。
另一些人则借助楷书而涉其他,有了新的拓展。王羲之、王献之同为小楷好手。尤其王献之的《洛神赋》,优雅清新,亭亭玉立,后世以之为范。然而,如果二王仅擅长小楷,不及行草,也就不是今日所说的“二王”了。写意精神使二王拓宽了行草书的审美空间,个人的精神世界也丰富充盈起来。王羲之的《丧乱帖》《孔侍中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鹅群帖》,都展示了与小楷全然不同的空间表现形式,再不是排列如算子、大小相等同,而是情性涌动、不可囿守。
欧阳修说得好:“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一个人会写小楷,又会行草书,一人之肉身,两种之精神。待到行草挥洒时,心已脱略笔墨畦町,云游龙骞,清风自适。行草书极大地开掘了沉潜于书法家内心的能量,开启了与工笔不同的跌宕激荡的精神历程。此时的空间运动发生变化,参差无定,疾徐互动,或大或小,或断或连。除了遵守书法的常道之外,更是于常中见新变,不拘形态,具有不确定的指向、不确定的结果。
戴叔伦诗曰:“人人细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其中的美妙,不可直陈,唯意会能得其真谛。行草书的变化无所不有,就像名字“羲之”,可信手以不同形态出现。行草书由正而奇,见出奇妙、奇异、奇肆,而得奇气、奇趣、奇境。其感性用笔,放胆而行,不在于写妍写丑,只是乘兴信手,超越常规。我本快意,写了再说——这种情性驱使畅笔无碍的行草作品进入一个无限延展的时空,给后人以横无际涯的想象。正是行草书,使书法家的真情性罄露出来。
而今我们读张旭、祝枝山、张瑞图、王铎、傅山这些书法家的作品,有楷书,也有行草,甚至是狂草。仅以楷书来认知一个人是不够的,只是看到了作为书法家的基本素养、技能,不能尽兴,不能尽其根本。就如一个宝藏,大部分在深处未能发掘提取。正是行草书展现出他们的才气、情调。人在行草世界里,意居先笔居后,纵横捭阖,行止无端波澜自阔。如果是狂草,则速度似流星闪电,气势如骤雨旋风,夸张开放,时在意料之外。
唐人任华曾说怀素草书“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书法家沉浸其中,已非俗世中人,只写意不写实。“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这就是恣情写草书的巅峰状态,倾泻而出不可阻遏。于是行草书多有奇气,有别于楷书的端正静穆。清人刘大櫆认为:“奇气最难识,大约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行草书正是借助书法家的小写意或大写意,以意为之淋漓痛快,使欣赏者观之,神秘莫测,不可实说不可测量,难以一眼洞尽。
古人书写有时得佳作,便有“如有神助”之说,因为行草书变化莫测,趋奇走险,绝不可能如楷书规划停当再下笔。在人们难以言说行草书书写时的莫测状态时,总是会称之为“神笔”。正中求奇,常中有变——循艺文之道的书法家大抵如此。起始按规矩行,得法。而后意大于法,不为规矩所缚,尽可能最大地释放个人的能量,探究更为辽远深邃的精神意蕴,而不止于狭隘的审美度量。这就需要循旧辙而开新境,追求有新意、有难度的创作。工笔创作,更多地得于技,以耐性沉稳而作。意笔创作以意驭笔,以行草书拉开与楷书的审美距离,显示出书体间不同的审美价值。
如果把王羲之、王献之的小楷与行草书对比,它们的差异性是很鲜明的。尽管小楷字数繁多,却无多少让人玩味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韵外之致。而行草书字数无多,幅式不大,却充满了这些审美要素。人们通过行草书看到了跃动不息、鲜活旺盛的生机,千年过往依然如此。
(作者:朱以撒,系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